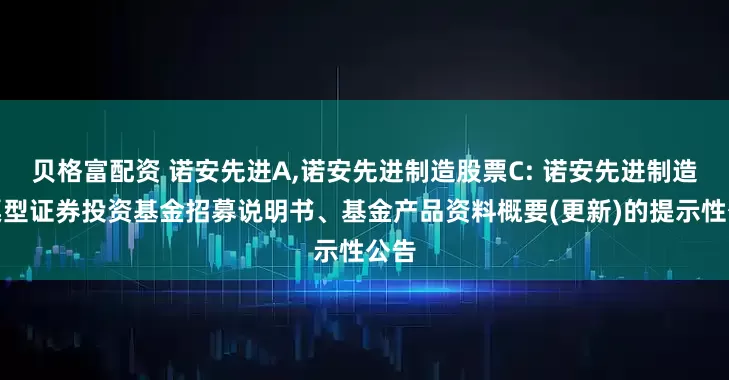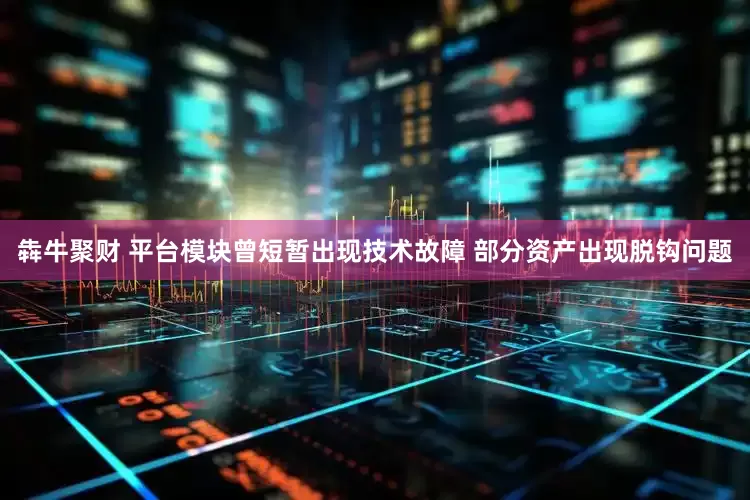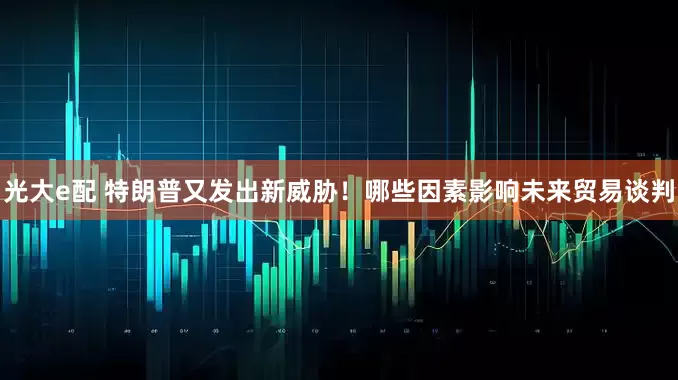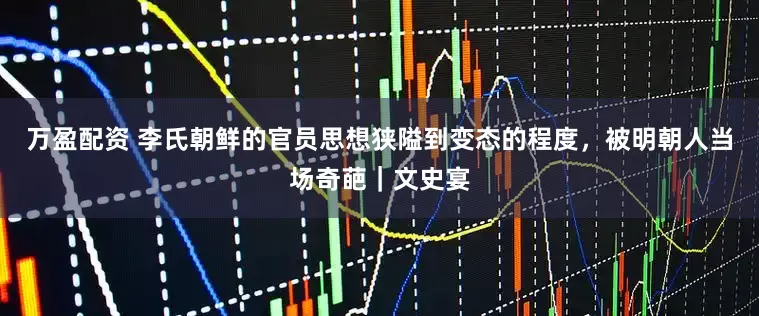

因为微信推荐机制的更改万盈配资
如果您喜欢敝号
请进入敝号页面点亮“星标”
这样不会错过好文推荐
文/广成子

朝鲜官员鲁认在万历援朝之战中流落中国,竟然参与了理学与心学之争,尽显朝鲜人对理学的执着和思路的狭隘,胡吹朝鲜军队不比日本差更是遭到防范质疑,总而言之,他对明朝的幻想跟实际颇有距离,因而生活之中经常发生龃龉,可见刻板印象确实会妨碍交流,古代更甚。这是一个系列故事文章,因为作者创作时间间隔较长,是断开推送的,推荐没读过前文的朋友读完下面专题里的链接再读本文,阅读体验会非常好。

请输入标题 bcdef
本文欢迎转载。
朝鲜官员明朝游记专题

虚夸朝鲜的军事实力

经过昨日一场激辩,鲁认也不好意思再去明道堂。本着不空入宝山的心态,他敲开了倪士和的房门,想向这位武夷山紫阳书院的讲学宗师求教止修之学的要领。倪士和对昨日的争论毫不介怀,欣然援笔,书示如下:
吾儒只宗孔圣,而孔圣之学,只在大学经一章。盖大学之道,论主意则只是止于至善,论工夫则却是教以修身为本。止于至善者,修身为本之命脉也。修身为本者,止于至善之窍门也。要将此数语,反覆参商出来复我,不要当做话头逗住。
大意为:儒门师法孔子,推崇《大学》。而大学之道以修身为本。朱熹阐释大学之道时认为修身要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养性,达到至善,是为八条之功。而见罗先生李材由八条发衍出止修学说,认为“止为主意,修为功夫”,至善则是目标。
鲁认将这几句止修之学的奥旨抄在纸上,道谢后回到房间。经过一昼夜的反复参究,他将自己的心得写在纸上,翌日一大早呈与倪、谢二位秀才案前,只有短短数语:
盖至善者即吾之性,在天为命。大学之道,只是一个止于至善。但止于至善,在何处着落,全在修身为本上见。
谢秀才(谢兆甲)阅后赞赏不已,称赞鲁认有闻一知十之能,当下与倪士和商议午后去拜谢徐宗师的引荐之德。鲁认思忖再三,觉得自己也应当去向徐宗师亲自表达谢意,于是又写了一篇文章,其中有“哪知今日万死之余,亲到乎此哉!非徒千古一奇会,似值古人穷亨之数,此所谓出幽迁乔者”的句子。

面对一代大儒的关切,鲁认老老实实承认日本兵将凶悍,凭朝鲜的武力绝无反攻对方国土的可能,唯有广布间谍、大兴水军才是切实可行的应对之道。徐即登深以为然,宾主晤对移时,乃揖别辞去。
五月十八日,坐营司总兵杨洪震派门子来请到府一叙,鲁认欣然前往。杨洪震率众衙客亲自迎接,庆贺他能得到一代宗师徐即登的青睐参讲书院,实乃千古奇事,就连金军门听说了也为你高兴。
鲁认再拜致谢,感念杨洪震平日之厚待。杨洪震则表示我并非只是同情你的境遇,更欣赏你的才华。当晚就在衙中设下酒宴为鲁认送别,宾主吟诗唱曲,尽欢大醉。杨洪震命士卒背上鲁认的行李护送其返回两贤祠,自己又与一众衙门人员亲自送到门外,再三殷殷拜別,各自有黯然神色。
五月二十日,众秀才又齐聚明道堂,写字条请鲁认前来为他们解惑。鲁认打眼一看,当场尴尬症又要犯了,原来字条上询问:
贵国强兵,素闻天下。隋唐之际,何其壮也。平秀吉之乱,何其脆弱之甚也。今公在倭得还,其虚实强弱,必如指掌。不徒孟浪,幸举一当以示也。
文中所谓“隋唐之际,何其壮也”,指的是一千年前高句丽王国与隋炀帝、唐太宗的历次战争。由于时代久远、文献混淆,明末的文士往往将朝鲜的高丽王朝与中国的高句丽王国混为一谈,因此疑惑武德如此充沛的朝鲜为何被区区日本打得一溃千里。
面对这样直率的提问万盈配资,鲁认臊得想找个地缝钻进去,但民族自尊心又不允许他嘴上吃亏,只得硬着头皮写字作答:
我国当隋唐之际,何其状也。辽州拒契丹、龟州之御蒙古、云峰之讨倭贼,素表表著称者也。而自古及今未尝有外海之侵犯王京,遂至此平秀之乱。我国累百载太平之余,大贼三十万乘其不虞,速战深入,疾如风雨,旬月之内。尽陷三都。
……大概丁酉之败,乃鲁鸡之不期,蜀鸡之不支。若使我国之兵,深入日本便作穷寇,则强弓毒矢,剽悍精锐,彼焉能当之哉!
为了挽回颜面,鲁认不遗余力地列举了朝鲜历代抗击外敌的“赫赫武功”,接着话锋一转,将战争初期的大溃败归因于日寇集中庞大兵力打闪电战,并且玩起了偷换概念,开始假设如果朝鲜军也集中兵力进行突袭,日本照样也会一败涂地。
眼看在场的秀才们面露疑色,鲁认不得已又往回找补,开始客观分析起他所观察到的日军优势:阵型、土垒作业。
但彼贼所长,非但鸟铳枪剑,虽行师野营苍黄临战之时,必集土垒于瞬息然后接战。故倭阵未易攻破。盖彼贼长得垒法之妙矣。
这时有人提问:“天下强兵,各骋精强,浙兵素称倭寇克星,然否?”鲁认作答:“我在本国时,细看南北之兵。平原广野则北方铁骑为上,山路径溪涧则南方步兵为上。”众人连连点头称是。
这里说句题外话,作为战争亲历者,鲁认的这句回答确实符合战争中明军的真实情况。根据相关文献,浙江义乌兵在万历朝鲜战争期间被朝廷作为抗倭克星大量征召,他们在戚家军将领吴惟忠、王必迪等人的率领下转战朝鲜,血战日军,为最终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由于军纪严明、作风优良,他们深受朝鲜君臣百姓的爱戴,被崇敬地称之为“红衣天兵”(大司马按,因为讨要欠饷,明朝下套把他们杀光光)。《锦溪日记》中的这条记载,可以视为一个佐证。


朝鲜人参加中国儒教典礼

五月二十三日,鲁认听说谢秀才(谢兆甲)精通《心经》的妙旨,于是上门求教。该书由南宋理学家真德秀所编撰,辑录了《尚书》《诗经》等古籍中关于心性修养的论述,并附有朱熹等人的注释,为视为理学经典。
早在十三世纪的元代,朱子学就从大都传入朝鲜半岛的高丽王朝,性理之说迅速风靡一时,到了李氏朝鲜时代成了独尊之官学。二百余年来,如郑梦周、退溪李滉等理学大师层出不穷。其中退溪李滉就对《心经》有甚深研究,曾宣称:“吾得《心经》,而后始心学之渊源,心法之精微”,并将自己的理解写成《心经附注》。
鲁认自幼研读理学,正是退溪学派的忠实门徒,这次机缘巧合进入书院学习,正想向天朝上国的学者好好请教一番有关《心经》的奥旨。面对他的诚心求教,谢兆甲欣然笔示:
心经只究人心道心之分,而经之主意,则只是一个敬字。盖敬者,主一无适,而常惺惺法,无一物不得容其中。故圣贤彻上彻下之功,都在敬而已。若不以敬操之为心上之功,则纷华波动,发如奔霆,莫知其乡矣。……且吾道一以贯之,则盖一者,乃精一之一字,只分人与道之间。以敬操之而已矣。
谢兆甲将心经概括为一个敬字,认为只要常怀惺惺之意,作宇宙万物皆可不纷然在目。而朝鲜退溪学派同样认为“心之工夫上着眼,一以敬为要”、“亦曰主一无适也,曰恐懼戒慎也,主一之功,通乎动静,戒懼之境,专在未发,二者不可阙一”,与闽学的“修心主敬、主一之义”学说份属同源,自然息息相通。
当下鲁认心有所悟,援笔答道:“以工夫论之,精一乃诚正修,而厥中乃止至善。本性之全体浑然,至善本无过不及之差,未知如斯否?”谢兆甲看了连连点头,认为鲁认已经明了心学之体,折衷比喻十分恰当,自己没什么可以教的了。
五月二十四日,鲁认晚饭后在两贤祠遛弯,发现有四十几名秀才齐聚明伦堂,似乎在进行什么演练。一问方知,原来万历皇帝颁布了平关白(丰臣秀吉)的黄麻诏,福建省由行人司正(官职名)李如珪负责宣读。而李如珪与徐宗师曾同拜李见罗先生为师,因此广邀芝峰、谨江、三山等书院的秀才同来聚会,准备明日在明伦堂举办大型讲学活动,现在大家正在作演礼准备。
不多时,徐宗师(徐即登)亲自来到两贤祠,与众秀才揖让见礼。按照他的指示,众人把三献茶、唱歌词、敲钟磬等礼仪流程演习了一遍。听宗师说,明日省内的各级大领导均会莅临参观讲学,千万不能出纰漏,务必演习熟练。鲁认思忖此次际遇难得,暗自期待不已。
翌日午前,徐宗师再度来到明伦堂,催促众位秀才把演礼流程又演习了好几遍。鲁认也夹在行列中模仿着进退揖让,却被徐宗师出言阻止:“你本是朝鲜人,参加此会乃千载奇遇。但行人司还没听说过你的来历,贸然在列只怕有所唐突。不如你先退回房中,等诸位老爷参加完毕再叫你出来。”
鲁认唯唯而退,回到房中不免心中有所失落,一时技痒,拿起笔又挥就一篇短文,表示自己虽是藩邦之人,自幼欣慕上国冠裳,恳请诸位老爷“勿拒善变于华者”。
刚放下笔,只听屋外钟磬之声大作,开窗查看,福建左佥都御史金学曾、行人司行人李如珪、左布政使朱运昌等大小官员鱼贯而入,各升阶上,免不得各自谦让一番,次第坐定。
这时鲁认方才敢从屋内出来,请倪士和代为呈上刚写的文章。李如珪阅后发问:“他一个朝鲜人怎么跑到这边来?” 徐宗师(徐即登)将鲁认的经历详细说了一遍,李如珪连胜赞叹:“他的命贵得紧、贵得紧。”
金学曾派人召唤鲁认来相见。鲁认赶紧趋到庭前,模仿秀才们的礼仪三揖行礼。相见完毕万盈配资,只听钟罄之声又起,讲学演礼仪式正式开始。鲁认侍立廊下,屏息观礼,只见:
秀才五人,趋诣尊所,亲奉茶碗,进献诸相前。单揖而立,诸相起立奉碗,置于案上,答揖以后,坐而饮茶矣。退碗则门子奉进,如是者三次以后。
执礼秀才一人,出立前列,高拱高声曰:进讲案!秀才二人,置心经及大学于大案上,两手对举,齐眉置于堂中。
执礼又出高声曰:唱歌词!秀才三人,列立东边,歌咏关雎鹿鸣之章。秀才二人,分立东西钟磬边,相击相和。激激切切,清朗铮然。满堂拱默,气定神清,自然有荡涤消瀜底气像矣。
唱歌词完毕,执礼又出班高叫:进讲!这时有秀才二人走到庭前,先讲经典一章,又由经文引申到“止修”二字,互相质问辩论,向堂上诸官请教。徐宗师在一旁随问随答,语言精奥,大抵如下:
尧舜以上,则皆以生知传于生知,故只有惟危惟微之分,遂及再传于禹,又加八字之烦。盖学问之原,自此始矣。而惟精惟一之学,误之者久矣,牛马同宗,吕嬴并秦。寥寥千载,岂不寒心云云。
徐宗师宣讲一通,向在座的诸公询问是否有所疑义,大小官员全都拱袖连称不敢。唯有师出同门的贵宾李如珪开口,二人互相质证,洋洋洒洒如江河东流,在场诸人无不悦服。

不多时讲学结束,进入休闲茶话时间。李如珪又指着鲁认感叹:“他的命真是贵得紧。” 徐宗师趁机推荐道:“他虽是朝鲜人,诗文也是极妙的。” 李如珪随即发表了一通明朝官员对朝鲜的奇怪认知:
那边国风好,喜诗。秀才之子做秀才,武弁之子戴武弁,荫官之子做荫官,宰列之子做宰列,谏臣之子入霜台。一自箕圣之东,文献之风有素矣。
这很显然又是因为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刻板印象。朝鲜李氏王朝诚然陷入阶层固化的怪圈,却也还不至于保持如此“上古之风”。鲁认本人就是经由科举晋身士大夫的例子,只不过他似乎很满足于这种正面的刻板印象,也就不再像前几日那般哓哓辩诬。
参讲仪式完毕,天色已暮,众位官员一一散去。这时其他书院来参会的秀才们慕名拜访鲁认,写字条想请教朝鲜国的礼义风俗。鲁认欣然应允,当众悬灯笔话,一一详作解答,满堂无不叹服。这场聚会竟从黄昏一直持续到了子夜,方才依依惜别。

朝鲜人维护理学、憎恶心学
到了变态的程度

翌日,鲁认仍沉浸在昨日那一番奇遇的兴奋之中,一大早又跑去倪士和的房中,表示昨日徐宗师所讲的那一章经文太过深奥,在下驽钝,只听了个大概,想请教它的精微之处。倪士和微笑笔答:“修身为本者,止至善之窍门也。止于至善者,修身为本之命脉也。鲁先生只要熟读徐宗师所赠的《闽中问答》,其精微妙旨字在其中。”
鲁认还想继续请教,倪士和直接点明了徐宗师(徐即登)赠书荐学的真实用意:希望他回到朝鲜后能把这些典籍付梓出版,将闽学的要义加以推广宣讲。如此朝鲜则人人向学,臣民皆孝悌忠信,尊亲君长,国家也就自然会随之而复兴。
鲁认这才明白了徐即登引荐他的真意,当下欣然允诺,表示自己定然不负诸位大贤的嘱托,如果能平安归国,一定将闽学的要义传布东方。日后他也确实信守承诺,在故乡的锦溪亭设坛开讲,将止修之学在朝鲜半岛加以阐扬。
明白了徐宗师的用意之后,鲁认便不再频频求教,开始与书院中的秀才们从容交游,一同观书赏花,拈韵作诗,乐得逍遥自适。

五月三十日,徐宗师冒雨来到两贤祠,将自己的一篇文章亲自誊写在明道堂的北壁之下。文章开篇则直斥陆王心学为以佛老僭冒儒学的异端:
近有一种学术,闻略于心身间,而以超脱为入微,以融通为妙悟。听其言,分明出老入释。究其学则曰:孔子孔子,人亦往往以孔子学目之。此其为害。盖不浅浅也。
后文又列举了孔子之后有《大学》垂世立教,创立“在明明德”、“止于至善”的宗旨,而这些又被朱熹归纳为“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八字条目,然后得出结论:性理之学才具备儒学正统性。接着文中提出修止学说的倡导:
由斯以谈,吾身联属乎家国天下,步步莫非实际,岂不广大?吾身完具此心意知物。种种皆是真修,岂不精微?然实实落落,不求之家,不求之国,不求之天下,而全副精神,直归向里。吾正吾心,吾诚吾意,吾致吾知,吾格吾物。一毫荧惑,不及其他人,岂不易简?此孔子尽性之学也。
在文末,他仍不忘再影射一把陆王心学为异端邪说:
知此者,谓之知本上此者谓之止善。识此者谓之识仁。而异乎此者,谓异端。有志之士,吾愿其共明此学。
一篇文章骂完还意犹未尽,徐宗师又分别在两壁的小屏风上题字。其东壁的文字引用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士君子不可无此功业。”
西壁则直接骂街,把陆象山、王阳明贬为以学术杀人的异教徒:“以嗜欲杀身,以虐政杀民,以货财杀子孙,以学术杀天下后世。士君子不可有此罪过。”
需知福建本是朱子学的大本营,而两贤祠内又无一不是闽学的门徒。徐宗师文章中提到的“有志之士”也好,“士君子”也罢,自然指的是来自朝鲜的鲁认。而鲁认对此表现出了无比赞同,他在日记中一字不漏地转载了全文,还在结尾作了高度评价:
盖此文,排斥陆象山王阳明学术之误,而倡明孔曾传受经一章蕴奥之旨。与见罗李先生,倡和一世,天下归宗焉。
所幸徐即登诸人的一番苦心孤诣终非虚掷。自从李氏朝鲜将朱子学定为官方意识形态以来,半岛上的学者便进入了一种皈依者狂热的状态,开始奉朱熹为孔、曾以来的唯一嫡派正宗,认为其余学派皆为异端邪说而大加挞伐。
十五世纪初,阳明心学传入半岛伊始,便遭到朝鲜学界上下一致的强烈排斥,无数朱子学的信徒群起“攻乎异端”。一代名儒退溪李滉曾直接下场开怼王阳明的《传习录》,特意写了一篇《传习录论辩》隔空对线,开篇痛骂道:“阳明乃敢肆然排先儒之定论,妄引诸说之仿佛者,牵合附会,略无忌惮,可见其学之差而心之病矣。”

万历元年(1573年)出使明朝的朝鲜使臣李承杨更加狂野。当时明朝太仆少卿魏时亮上奏请求将王阳明牌位从祀孔庙,奉敕命将奏疏下朝堂议论。朝鲜使臣李承杨不顾礼仪当庭抗辩,厉声斥骂魏时亮”诽谤理学、背谬圣贤、蛊惑人心”,进而滔滔不绝地表示朱子学乃是孔门唯一正宗,堂堂天朝岂能让异端分子玷污神圣的儒学殿堂。
面对举朝惊愕的明朝君臣,他竟然手书六个大字双手举起:“王阳明,邪臣也!”只留下年幼的万历皇帝在风中凌乱。
无独有偶,万历二年(1574年),朝鲜使臣许篈出使明朝,曾在辽东正学书院与贺盛时等四位生员进行笔谈:“窃闻近日王守仁之邪说盛行,孔孟程朱之道,鬱而不明云,岂道之将亡而然耶?”
四位生员被问得一头雾水,以为他对阳明之学有什么误解,当下好言相劝:“本朝阳明老先生学宗孔孟,非邪说害道者。比且文章、功业俱有可观,为近世所宗,已从祀孔庙矣。公之所闻意昔者伪学之说惑之也。”
不料这一下点燃了许篈作为朱子学信徒的卫道士狂热,奋然笔走龙蛇,写下数百字对阳明心学的批判:
独王守仁者,拾陆氏之余,公肆谤诋,更定《大学章句》,其言至曰:苟不合于吾,则虽其言之出于孔子,吾不敢以为信然也。推得此心,何所不至。守仁若生于三代之前,则必服造言乱民之诛也。夫守仁之学,本出于释,改头换面,以文其诈,明者见之,当自败露。
阳明之所论著,千言万语,无非玄妙奇怪之谈,张皇震耀之辩,自以为独得也......且世之所推阳明者,以其良知一说也,而愚窃惑焉……今如阳明之说,则是弃事物、废书册,兀然独坐,尽其有得于万一也,乌有是理哉?此阳明之学所以为释氏之流而不可以为训者也。
许篈在文字中竟将阳明直接贬为惑众左道之流,不可谓不偏激。碰巧这四位生员也是典型的东北人,全然不惯着这位远道而来的朝鲜官,当下也是奋笔疾书反驳。双方你来我往,笔战往复不休,谁也说服不了谁,一直辩到纸尽墨干,彼此精疲力竭,只得不欢而散。
目睹到堂堂中华学子竟然支持“异端邪说”, 许篈深感不可理喻,他在《荷谷先生朝天记》中慨叹:“由此观之,则今之天下不复知有朱子矣!邪说横流,禽兽逼人,彝伦将至于灭绝,国家将至于沦亡。”

长期抱有这样的刻板印象,再加上壬辰战争期间宋应昌等人对心学积极的宣扬,朝鲜君臣一度误以为“阳明邪说”真的成了中国儒学主流,而朱子学已近乎无立锥之地。一直到鲁认归国后,朝鲜学者柳成龙、许筠等人看到了《锦溪日记》相关记载,这才了解到中国仍有不少坚持朱子学的同道中人。
其中礼曹判书尹根寿在奏对中提到从鲁认日记中所见闽儒排斥陆王的记载,对其大感欣慰:
臣又闻即今江西人徐即登,翰林出身,而提学于福建,讲学武夷山紫阳书院,力排陆九渊王阳明异端之学,名振中外。凡于福建、浙江学宫屏风,即辄以大字书王守仁之过失,曰以虐政杀民,以宝货杀子孙,以学术杀天下后世。
由此可见,即便在四百年前,国家与国家之间也需要来自各种渠道的直接交流,否则就很容易因为刻板印象产生天大的误解。机缘巧合之下,鲁认此次在福建的见闻从某种程度上增进了明、朝两国之间的人文联系,不可不谓弥足珍贵。
欢迎关注文史宴
专业之中最通俗,通俗之中最专业
熟悉历史陌生化,陌生历史普及化
金港赢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